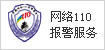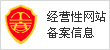文学
捕蝉忆趣
捕蝉忆趣
徐西江
“牧童骑黄牛,歌声震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一首唐诗活画出一幅夏日捕蝉童趣图。如今夏至已过,窗外绿杨间蝉鸣悠扬,忽然忆起童年捕蝉的趣事来。虽然年久月深,时过境迁,那情那景想起来仍觉意趣盎然,不由不捉笔记之。
蝉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在我的家乡山东省郯城县,人们称蝉为“姐儿”,称它们的幼虫为“姐儿猴”。小时候只是人云亦云地如此叫它,不知这小小的生灵为何却有这般拟人化的“乳名”。现在想来,大概把蝉称作“姐儿”是因为她的美丽、轻盈、善歌,把它的幼虫叫做“姐儿猴”是因为它们憨态可掬、善于攀援吧?家乡人如此命名却也准确生动。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的美丽是毋庸置疑的,历代文人墨客多曾描绘过她美妙的身姿和动听的歌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古人亦曾赋予蝉深刻的寓意和哲思。但这些都是文人雅士的事,小孩子们不懂,他们更痴迷于捕蝉的乐趣。的确,小的时候,捕蝉是漫长夏日里最好的游戏了,比下河扎猛子,比爬树摘果子,比钓虾子、扑蜻蜓、捉蚂蚱都更有一番情趣。
骑黄牛的牧童是如何捕鸣蝉的?用的是什么工具、什么方法?诗歌里没有提,所以也就无从考证。而我小时候和玩伴们捕蝉的方法却有好多种,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夏至过后的五个星期是蝉结束漫长蛰伏、出洞见天日的时节。傍晚,人们拿着刨铲、水壶、手电筒、细竹竿和瓶瓶罐罐的容器,陆续走出家门。父带子,姐携弟,好玩伴,好兄弟,两个一伙,三个一群,从四面八方踽踽而来,加入逮“姐儿猴”的大军。村道旁、菜畦边、篱笆下,小河畔、树林中、场院里,只要附近有树和灌木的地方就是逮“姐儿猴”的好去处。椿、榆、桐、槐、桃、杏、梨都是蝉爱栖息的树木,杨、柳则是它的最爱。
抓“姐儿猴”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无外乎三种:
一曰“请君出瓮”。经过仔细搜索地面,你会发现一个不规则的小洞口,用手指轻轻一抠,洞口豁然变大,一个神秘深邃的圆洞就出现在眼前。此时,就会有一个三角形的脑袋冒冒失失地探出洞口,随后前腿也伸出洞来,你轻轻捏住向上一提,一只胖乎乎、傻愣愣、憨态可掬的“姐儿猴”就成了你的俘虏。也有警觉的,看到情况不对立马缩进洞里,任凭你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这时你可以放进一根细细的小木棍,好奇的洞主就会技痒难耐,沿着木棍儿表演“猴子爬杆”,乖乖地爬出来举手投降了。偶尔会遇到负隅顽抗的,那就只能水淹七军了。现成的小水桶,只需把洞给灌满,半分钟后,水落“猴”出,一个满头泥水、异常愤怒、忍无可忍的家伙就会舞动着“双刀”出洞迎战,当然,不出意外的话它败给了入侵者。
二曰“满地搜寻”。那些自行破洞而出的“姐儿猴”们,正在兴奋异常地满地乱爬,急切地寻觅合适的树干、灌木以备蜕变成蝉,羽化升仙。这时只需在地面上、草丛中仔细搜寻就行了,没有什么技巧,眼尖的多得。遇到癞蛤蟆、蛇也是常有的事,——它们也觊觎这美味的“姐儿猴”大餐,眨眼的功夫就能吞下一只。不期而遇后,孩子们大多也并不十分害怕,躲开就是了;也有胆大顽劣的,抓了癞蛤蟆吓唬同伴……
三曰“树上排摸”。随着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侥幸躲过前两轮搜捕的“姐儿猴”们已经爬上了树干或灌木的枝梢。此时,早已备好的手电筒派上了用场,沿着树林,一棵树一棵树挨排照下去就是了。随时都能发现目标,低处的伸手拿来,如探囊取物,高处伸手够不到的用竹竿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然后从地面或草丛里找到它就大功告成了。有时不小心会在草丛里摸到一种黄褐色的小蛙,凉凉的,心里一惊,大叫一声丢开去,笑骂一句,引起小伙伴们的一阵哄笑,仅此而已。
记得在沭河岸边一个绵延数公里的杨树林里,晚上会有数百上千人参与逮“姐儿猴”比赛,手电的光芒明灭闪烁,人声喧哗如夜市,场面十分壮观。从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到夜色深沉凉露初生,兴致勃勃地抓了几个小时,累了、困了,尽了兴,就收工回家,常常是满载而归。一晚上抓到几十只上百只甚至数百只“姐儿猴”司空见惯、并非难事。
对付呆萌笨拙的“姐儿猴”,方法简单粗暴,没啥技术含量;而要抓住那些躲过搜捕完成了蜕变、经历风露加持了技能、展翅高飞攀上了高枝的“姐儿”们,却颇需一些真正的“技术”了。由于难度翻番,抓“姐儿”更具挑战性和趣味性,小伙伴们更是乐此不疲。
抓“姐儿”的关键技术凝结在三个字上:粘、扣、诱。单从字面上看就能隐约感到其中的阴谋、算计和杀机,但更多的还是其中的无穷乐趣。
“粘”者,用黏的东西吸附也。那个时候很难找到胶纸、胶带、化学类的黏胶,只能就地取材。往往是从家里偷偷抓一把麦粒,放到嘴里不停地嚼,直到嚼出面筋,然后把这像口香糖一样黏到拉丝的东西粘在一个长竹竿的梢上,工具就做成了。三五个小伙伴循着蝉声,蹑手蹑脚地来到河堤边的柳树下,很快就锁定了目标。在长竿可及的柳枝上,一只双翅修长的漂亮“姐儿”正在卖弄歌喉,时而引吭高歌,时而浅吟低唱,全然不知危险的临近。此时,一根长长的竹竿悄悄地伸到她的身后,少停片刻调整好方位后,偷猎者手腕轻轻一抖,竿头向上一送,面筋和蝉身瞬间亲密接触。惊慌失措的歌者努力挣扎,凄厉哀鸣,可是黏黏的面筋粘住了翅膀、糊住了腿脚,再也无法挣脱。
“扣”者,牵住、勒住、套住也。这需要一根做扣的细丝,麻绳太粗,缝衣线太软,牛尾巴上的长毛柔韧、光滑、弹性好,堪堪可用。而要得到一根牛尾丝,饲养员是最大的障碍。小伙伴们费劲心思,调虎离山,多方掩护,终于从老黄牛“花花”的尾巴上“借”来一根上好的长毛。还是那样的长竹竿,只需在竿稍上打一个不大不小的活扣儿,套竿就做好了。同样的团队,同样的地点,同样急不可耐的心情。主套者擎起长竿,凝神屏息,围观者闭口而立,收心静气。一个若有若无的圈套向美丽的“姐儿”缓缓靠近,再靠近,掠过她的长翼,越过她的身体,停在她的头颈前,几乎要碰到她水灵灵的大眼睛。“姐儿”突然警觉,振翅急飞,然而却一头扎进圈套,活扣儿被她自己拉紧,勒住了脖子。场面顿时失控,上面的吱哇大叫,扑扑乱飞,下面的欢呼雀跃,手舞足蹈。随着长竿收回,狩猎宣告成功。
“诱”者,投其所好,引其就范也。和其它昆虫一样,蝉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小伙伴们在河滩上燃起一堆篝火,然后跑进附近黑魁魁的杨树林里,手脚并用晃动树干,原本安静的林子里顿时热闹起来。成百上千的“姐儿”们纷纷嘶叫着飞向“光明陷阱”,有的竟如飞蛾扑火直接飞进火中。此时,只需拿来一个容器,把这些向光而来的飞天来客捡拾进去就行了。
如今少年成翁,忆起童年捕蝉旧事,仍然趣味十足。现在的蝉似乎并没有比过去少,市场上仍然有卖,餐桌上也经常可见,夏日林子里的蝉鸣依旧热闹。然而,那种种捕蝉的乐趣,现在的孩子还会有吗?
热点信息
-
10月15日,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文艺期刊理论评论编辑人才培训开班仪式在中...
-
有灵气的文字,能让黑暗发光身为茶艺师,我的日常便是煮水、闻香、与静默对坐。茶,是我渡己亦渡人的一叶扁...